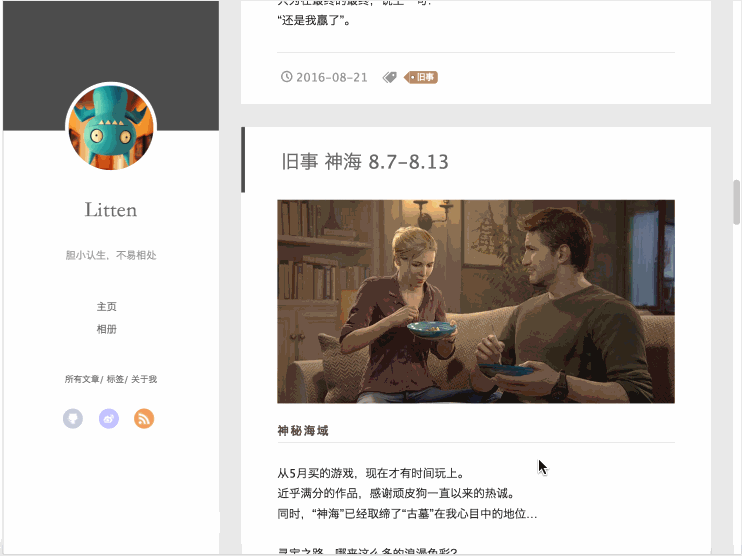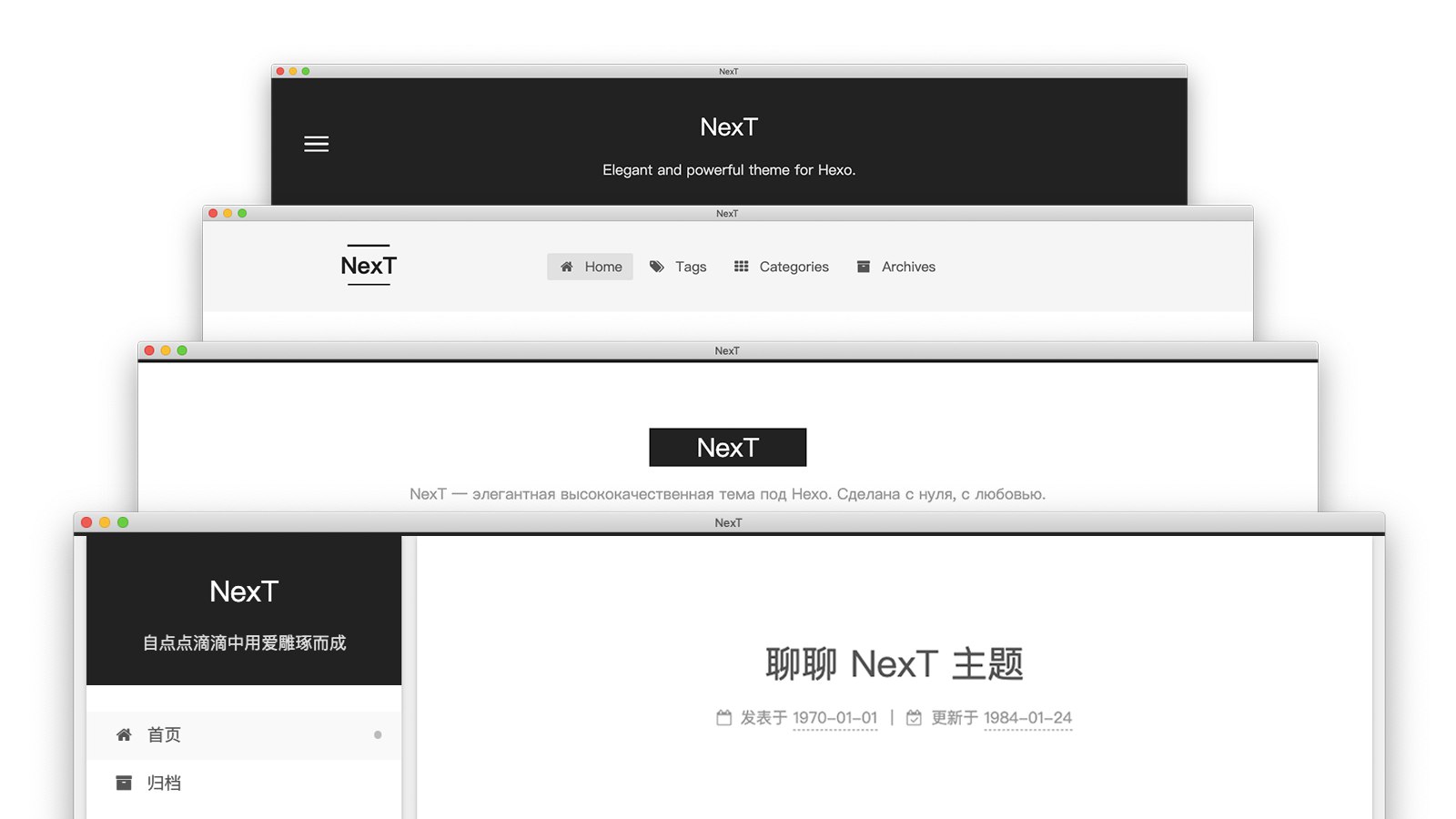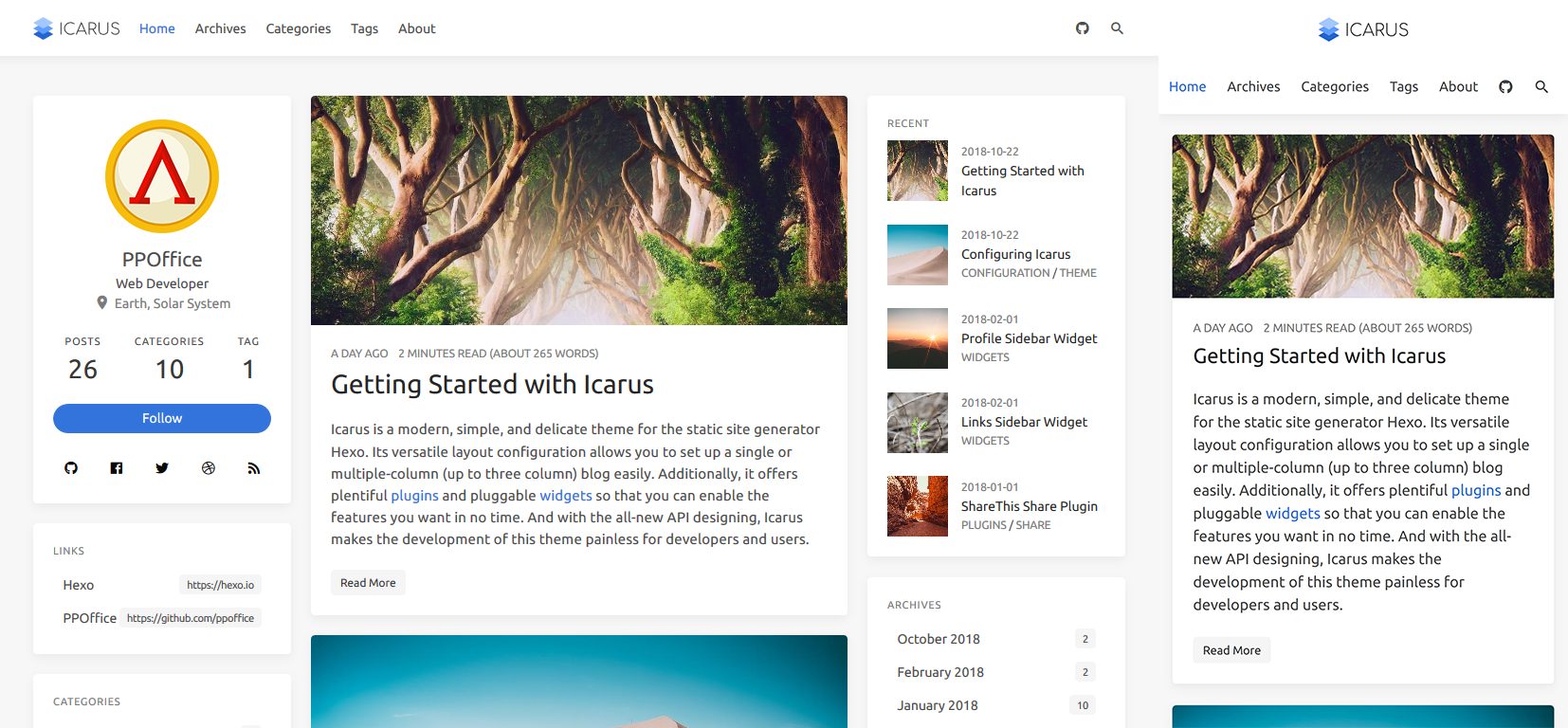山径上的木子香

山径上的木子香
xfm山径上的木子香
霜降过后,山里的风就添了些凉。清晨我还赖在被窝里,就听见院坝里竹篮碰撞的脆响,接着是奶奶的声音:“快起咯,今日日头好,木子该摘了。”
木子就是油茶果,村里人的“秋冬宝贝”。山后的油茶林种了几十年,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,深绿的叶子间缀满青褐相间的果子——有的壳子绷得紧紧的,泛着油亮的光;有的裂了道缝,黑红的籽儿露出来,像憋不住要探头的娃娃。奶奶总说,霜降后的木子最饱满,榨出的茶油才香,所以每年这时,全家都要上山“抢”时节。
我趿着妈妈的旧胶鞋,拎着小竹篮跟在后面。山路铺着一层枯黄的茅草,踩上去“沙沙”响,偶尔窜出几朵白色的野菊,沾着晨露,蹭得裤脚湿漉漉的。奶奶走在最前,蓝布棉袄的后襟被风掀起,手里攥着根竹竿,竿头绑着个铁钩——那是她用了二十年的“老伙计”,专勾高处的木子。“慢些走,”她回头喊,枯瘦的手指指向路边,“那丛刺莓红了,等会儿摘完果子来摘。”
到了油茶林,妈妈早找好一棵矮树,踮着脚摘低处的果子。“咔嚓”一声,一颗木子落在她臂弯的竹篮里,壳子上的绒毛还沾着叶子。“你捡地上的就好,”她笑着递过块布,“别碰枝桠上的刺,刮破手疼。”我蹲下来,把落在枯草里的木子一个个捡起来,指尖触到壳子,硬邦邦的,带着山里的凉。有的果子掉在石缝里,得用手指抠,指甲缝里很快嵌了黑褐色的泥,却一点也不觉得脏——这是山里的印记,带着木子的清苦香。
奶奶在高处忙活,铁钩勾住枝桠轻轻一拉,“哗啦啦”,几颗木子就滚下来,我赶紧伸手去接,却被一颗砸中手背,不疼,倒觉得热闹。“丫头,看那棵树!”奶奶指着不远处,“去年我在那儿摘到颗‘木子王’,比拳头还大。”我跑过去看,树干上果然有个浅浅的刻痕,是奶奶做的记号,枝桠间挂着颗圆滚滚的果子,我踮着脚够不着,急得转圈,奶奶笑着走过来,伸手一摘就递到我手里:“喏,今年的‘王’归你。”
日头升到头顶时,竹篮都满了。我们坐在油茶林的石头上歇脚,妈妈从布包里掏出红薯和玉米饼,还有个保温壶,倒出的热茶冒着白气。风穿过树林,带着木子的清香,混着红薯的甜,暖得人心里发慌。奶奶啃着玉米饼,说以前摘木子更辛苦,天不亮就上山,背着比人还高的背篓,走几十里路去榨油坊,“那时茶油金贵,过年才能舍得用它炒回肉,现在好咯,自家榨的油,天天都能吃。”
下午下山时,每个人都背着沉甸甸的竹篮,压得腰微微弯。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,山径上满是我们的脚步声和说笑声。到家后,妈妈把木子倒在院坝的竹席上,摊得薄薄的,奶奶拿着竹耙子,一下下翻晒,“得晒够三天,壳子干了才好剥籽。”我蹲在旁边,帮着把裂壳的木子掰开,取出里面的籽儿,黑红的籽沾着碎壳,放在手里沉甸甸的。
晚饭时,妈妈用去年的茶油炒了青菜,油花在锅里“滋滋”响,香味飘满整个屋子。奶奶喝着米酒,说等木子晒好剥了籽,就拉去榨油坊,“今年的籽饱满,榨出的油肯定香,到时候给你装一壶带城里去。”我夹了口青菜,脆嫩里带着茶油的醇厚,忽然觉得,这山里的木子,摘的是果子,晒的是时光,榨出的是一家人的烟火气——简单,却踏实得让人心里暖和。
夜里躺在床上,还能闻到院坝里飘来的木子香,混着晚风,轻轻落在枕头上。想起白天在山里的光景,奶奶的铁钩、妈妈的竹篮、我手里的“木子王”,还有那漫山的油茶林,忽然明白,农村人的日子,就像这木子,要耐着性子等它成熟,要亲手去摘、去晒、去剥,才能尝到最真的香。而这些藏在山径间的日常,正是最珍贵的时光。
- XFM 写于2025中秋夜